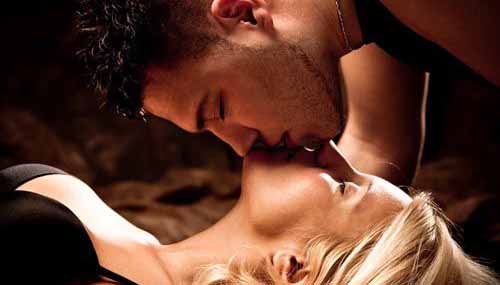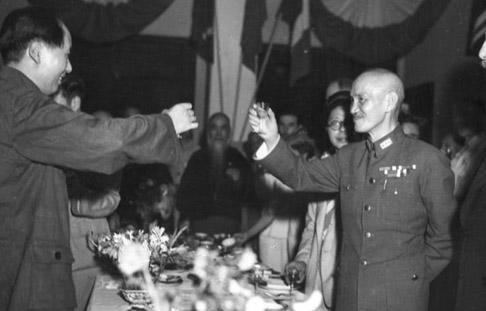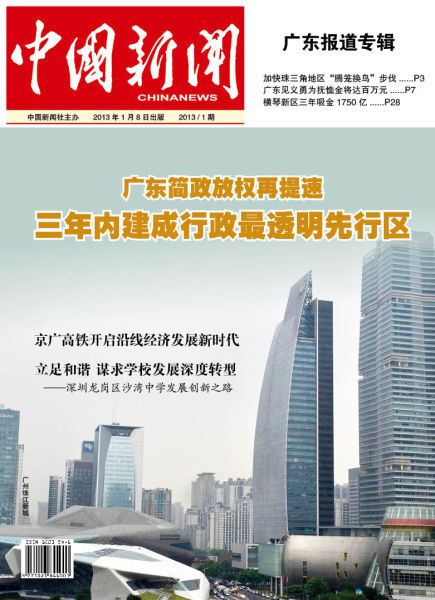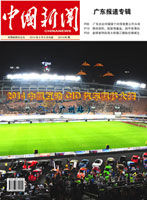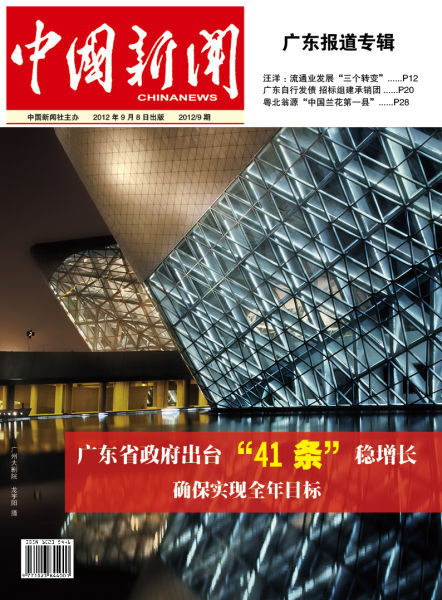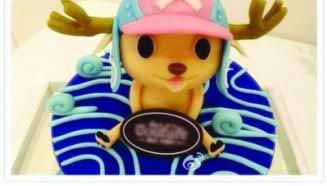潮汕听涛:从古诗词中读出潮语古味
- http://www.redrum-tech.com 2013年09月26日 13:04 来源:36365.com
-
□杜健生
略懂点古诗词的人都知道,古诗词在古代是可以直接拿来歌唱的,从许多古诗以行、曲为题目可略见一斑。因此,写诗填词都得受制于音韵(平仄及押韵)。也就是说,一首具体的诗词,其音韵都有固定的格式,不能随意改变。正如传统的民歌及小调,都有其固定的旋律一样,写诗填词也只能按照其格式,选择音调相应的字填入与之对应的位置。如现代歌曲,作曲家完成谱曲后,词作者填上歌词即可,不管填上什么歌词,这首歌的旋律和声调是永远不变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现代歌曲和古诗词的性质并无二致。只不过现代歌曲分作曲和填词两步完成,而古诗词即一次成型。
平仄是汉语发音的声调,讲究平仄是写古诗词的基本要求。古汉语将语音分为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四个音调,望文生义,“平”就是古诗词平仄中平声的字,其余“上、去、入”三个音调的字均是仄声。而现代汉语(即普通话)将语言的音调分为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。可以看出,现代汉语没有入声。但古汉语中属于入声的字仍存在,这些字都分散于现代汉语的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之中。其中归入阴平、阳平的字仍属仄声,写古诗词时应加以分辨,这给写古诗词的现代人带来很大的麻烦。但如果由潮州人来写,当无此虑。潮州话八个音调,分别是“上平、上上、上去、上入、下平、下上、下去、下入”。可以看出,潮州话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四个音调。因此,潮州人写古诗词得天独厚,可以免去辨认入声字的烦恼。试举王维五言绝句《相思》为例: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?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此诗的格式是“仄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,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”按其格式,第一句的“国”及第二句的“发”二字的位置应为仄声才合格,而按现代汉语的发音,这两个字分别是阴平(发)和阳平(国)。难道王维错了吗?当然不是,在潮州语音中,这两个字都是“上入”,属古汉语的入声,理所当然也属于仄声。同理,王之涣《登鹳雀楼》中“白日依山尽”及“更上一层楼”的“白、一”二字也是仄声,在潮语中属“下入”。
许多古诗词用潮语读来也十分押韵、悦耳。试以苏轼的词《满庭芳》为例:“归去来兮,吾归何处?万里家在岷峨。百年强半,来日苦无多。坐看黄州再闰,儿童尽楚语吴歌。山中友,鸡豚社酒,相劝老东坡。 云何,当此去,人生底事,来往如梭。待闲看,秋风洛水清波。好在堂前细柳,应念我,莫剪柔柯。仍传语,江南父老,时与晒渔蓑。”宋神宗元丰七年三月,苏轼接到由黄州调往汝州任职的诏命。闻讯,江南的朋友们都纷纷赶来相送,临别时,依依不舍之情皆溢于言表。感此,坡公即挥毫填此词遗友。整阕词用潮语读来十分顺畅,口语化的语言犹如小河淌水,让人感觉是与挚友在促膝倾谈,不舍之情在娓娓的倾诉中得到自然释放,令人一读难忘。
此外,潮语一些字在口语中的用法也古意盎然。一千多年前冬天的一个傍晚,彤云密布,大雪将临。白居易突然酒兴大发,于是就写了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至今,潮州人若问别人有何事何物时,还是将要问的事物直接放在“有”与“无”之间发问,句法简朴自然,语言干净朗爽,不易产生歧义。如:有会(会议)无?有水无?……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潮州话是古而不是土,潮人不要妄自菲薄。而现在潮州很多小学生,都操着潮语的音调说普通话,作为乡音的潮州话倒不会说或说不好了。不禁想起贺知章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的名句。我担心,长此以往,到头来孩子们的普通话既说得不准确,而却把乡音弄丢了,教师及家长当深思。(来源:潮州日报)
[编辑:nimo]
-